 |
您目前的位置:首页--行业分析 |
|
“低碳经济不仅是少用一度电或节约一滴水,更不是要我们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的节约经济”,它是发展问题,也是经济模式,是实现多方共赢得发展方式。哥本哈根大会结束不久,循环经济专家、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诸大建教授,在上海第28期文汇讲堂现场提出最新观点。
中国必须要走低碳之路
中国为何要走低碳之路,诸大建认为,一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二是自身发展的需求。来自外部的压力是碳的总量排放和人均排放:总量上看,在1997年-2007年中国的总量和人均都是低的。但是,自2007年开始,中国碳排放总量有明显增长,成为世界碳排放比较多的国家之一。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争辩权,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中的隐含因素和历史积累因素。隐含因素指,中国的碳排放很大比重是为发达国家生产了许多产品,有关的研究成果说,中国的碳排放量中有1/3是为发达国家而产生的。从中国出口隐含能源看,2006年较2002年出口额增长1.97倍,出口隐含能源增长1.79倍,说明有结构优化,但作用远远小于出口额的高速增长。从进口隐含能源看,2006年较2002年进口额增长1.68倍,进口隐含能源增长2.1倍,说明进口来源多元化带来结构性影响,但作用远远小于进口额的高速增长。可见,如何处理隐含能源的问题,将成为一个争议性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在争论,碳排放该由生产国还是消费国负责。
就积累因素而言,中国不能够为富国的历史排放承担责任,其中美国历史累计总量是最高的。据统计,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04年,每10吨二氧化碳中,有7吨是富国排放的,英国和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存量达1100吨,而中国人均存量为66吨,印度人均存量为23吨。
诸大建认为,外部压力和自我争辩理由都不是主要的,中国自我选择才是根本,无论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与否,中国必须走上减少化石能源的道路,否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就没有可持续性,将极大地削弱国际竞争力。
从中国自身发展来看,中国的形势刻不容缓。碳排放量遵循卡亚等式: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人口×GDP/人口×能源/GDP×CO2/能源,前两项都降不下来,中国能努力的就是后两项,单位GDP的能耗和单位的二氧化碳能耗,两者合起来就是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我国提出以2005年为基准线,到2020年减少40%-45%,按照刚才的公式,GDP如果保持8%的增长率,到2020年大概是2005年的3.17倍。即使单位强度按照目标降下来了,但是排碳总量还要增加70%-90%。中国未来的挑战会越来越严峻。这种最严峻主要不是来自外部压力,而是我们的经济模式必须要改变,要加强能源替代和提高能源效率降低。
仍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
诸大建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建设低碳城市;二是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三是提倡低碳的生活模式。
对发展低碳城市而言,每个城市需要考虑三个空间,建设用地的空间、农林空间和自然空间,如果前者具有排碳功能,后两者则具有吸碳功能。低碳城市应该有足够大的自然和农林空间,所以规划和建设首先不是做开发区规划思维,而是要做不开发区规划,要把碳汇空间固定下来,这样才能增加城市发展的低碳能力。
城市的低碳产业发展主要在三大环节: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替代及碳汇碳捕捉。具体来说,输入端的碳源减少,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转化端的能源效率,主要提高工业能源效率、建筑能源效率、交通能源效率;输出端的碳汇吸收,从生态挖掘到生态建设。( 责任编辑:管理员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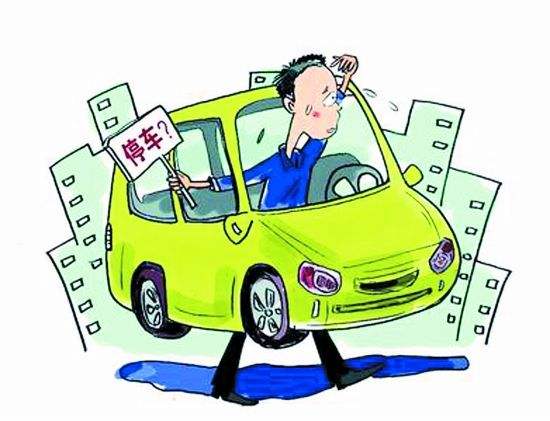 |
|
| 因地施策,破解停车难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