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您目前的位置:首页--国际交流 |
|
经历10余年停滞后,美国电力需求自2020年起反弹,2020-2022年间电力消费增长7%。电气化、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等板块的发展推动了新的负荷增长。在此态势下,变压器出现供应短缺。
政客们将矛头指向产业转移所带来的能源供应链危机,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交流电和变压器最早的应用市场,美国曾在电力工业发展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却因推行逆全球化,而逐步走到当前境地。
美国电气钢与变压器制造业的没落,是制造外迁、政策失衡与国际竞争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便当前有复兴呼声,但从基础设施、技术人才到成本结构的重建难度来看,这些产业的复兴都面临极大挑战。
从“电流大战”到现代电力工业时代
1882年,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下城珍珠街,世界上最早的商业直流电站建成,煤炭蒸汽驱动的直流发电机输出110伏的直流电,通过地埋铜线,供应85个用户、点亮约400盏电灯,输电半径不超过1公里。
受限于直流供电系统,尽管电力在19世纪末已广泛应用,发电站在规模、功率和供电范围上仍受到极大限制:在输电过程中,电压过低会导致电能损耗严重,无法远距离传输;而高电压又不适合直接用于家庭和工厂。
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改变电压的装置——在发电侧将电压升高,减少远距离传输的损耗,在用电侧将电压降低到家庭和工厂可直接用的等级——而这,就是变压器的作用。
1831年,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faraday)发现电磁感应,证明了磁场变化可以在导体中感应出电流,这为变压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真正意义上的高效实用变压器,由匈牙利电气公司ganzworks的三位工程师于1885年合作发明,这标志着现代变压器的诞生。
很快,一场围绕“使用直流电(dc)还是交流电(ac)”作为主流电力系统的激烈技术辩论与商业竞争在19世纪80年代末展开。这场“电流大战”(warofcurrents)大约从1886年持续到1893年,直流电阵营以托马斯·爱迪生为代表,交流电阵营则以尼古拉·特斯拉、乔治·威斯汀豪斯为代表。
1891年,特斯拉和威斯汀豪斯成功地在科罗拉多州和芝加哥之间长距离输电,展示了交流系统的优越性。1893年,威斯汀豪斯公司获得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照明合同,用交流电为整个展会供电,击败了爱迪生阵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895年,尼亚加拉大瀑布水电站(niagarafallshydroelectricpowerstation)建成,采用了特斯拉设计的交流电系统,成为全球首个大规模应用交流电(ac)系统的发电站,初期发电能力为2.5万千瓦,通过升压变压器,电站将电压从10,000伏升高到100,000伏,实现长距离输电。而上述匈牙利电气公司ganzworks正是变压器等设备的供应商。
现代电力工业时代正式开启。各国随后纷纷采用交流电系统,应用到大型水力发电站、火电厂等,电力得以广泛普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处于全球电气设备制造的领先地位。西屋电气、ge等公司不仅掌握先进技术,还推动了美国电网的标准化与规模化。
上游反倾销,下游产业转移
高压变压器往往重达几十吨甚至上百吨,对运输工具要求高,20世纪80年代之前,全球很多港口尚不具备处理超重货物的起吊设备。即使能海运到港口,内陆运输仍是巨大挑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球航运业经历了集装箱化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货物运输的效率和安全性。这一变革使得包括变压器在内的重型电气设备能够更便捷地进行跨洋运输,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增长。
这里不得不提到电气钢的发展。电气钢又称硅钢,是变压器、发电机等电气设备的核心材料之一。电气钢最早在20世纪初由美国的armcosteel(aksteel的前身)研发,从1970年代起,日本和德国在超薄高导电气钢领域取得领先。在这一阶段,日本、德国等国家的钢铁制造迅速崛起,依靠低成本和高品质产品抢占市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0年代后期,美国本土钢厂成本高企,设备老化,在遭遇外来钢铁产品竞争时,大批钢铁工人失业,美国本土钢铁企业请求政府提供保护。
1982年,美国政府启动“自愿出口限制协议”,要求日本、德国等钢铁输出国自愿限制出口美国;1984年,美国设定钢铁进口配额,控制钢材进口比例;1985年,美国开始对部分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电气钢供应链也因这些政策而受到影响。美国国内电气钢厂商获得了保护,但美国本土电气设备制造企业难以大量采购高性能进口电气钢,部分中大型变压器生产效率受限。
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美国变压器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至墨西哥与加拿大,以规避高关税与材料成本。
但对电气钢的反倾销并未停止。2000年后,aksteel成为美国电气钢领域主要生产商,频繁要求对进口电气钢征税。2002年,布什政府启动第201条钢铁保障措施,对含电气钢在内的多类钢产品加征关税。
2004—2007年,美国房地产繁荣期间,多个变压器制造商扩张产能以满足激增的电力基础设施需求。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企业遭受了严重冲击。下游不景气的同时,上游对电气钢的垄断并未停止。
2010年起,ge等多家下游公司公开向美国能源部反映“电气钢价格过高、供应不足”。这些企业不得不关停在美国本土的生产线,扩大海外制造基地。2014年前后,美国国内仅剩少数高端大功率变压器制造厂家。
2018年后,特朗普政府依据“232”条款再次征收25%钢铁进口税,电气钢被列入关键品类,墨西哥、韩国作为美国变压器主要进口来源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短缺现状与不确定的未来
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初步分析估计,当前,美国的配电变压器存量约为6000万至8000万台。预计到2050年,其总体存量将比2021年水平增长约160%至260%。
此外,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电气化推进,尺寸更大、功率更高的变压器需求将显著提升。
美国电网系统已经发出警报,发电项目、变电站建设排队待接入,数量巨大,电网改造升级迫切。
与此同时,供应端却严重吃紧。咨询公司woodmackenzie的报告显示,过去两年,美国变压器交付周期大幅延长——从2021年的约50周,延至2024年的平均约120周。而含变电站电力变压器和发电机升压变压器在内的大型变压器交付周期则在80至210周之间不等。
面对短缺,美国政府决定加大力度鼓励在本土投资建厂。在美国政府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一系列负面后果,这些投资还有可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并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
为此,美国国家工业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七项建议,旨在促进国内变压器的生产,并推动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以确保这种关键电网组件的充足供应。
政策一定程度上刺激部分厂商在美国本土建厂。2024年2月,西门子能源宣布,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投资建立其首个美国大型电力变压器制造厂。
只是,从产业结构看,美国在变压器制造环节仍面临劳动力短缺、电气钢等原材料稀缺、规格定制化严重、生产周期长等问题。美国国内制造商表示,劳动力短缺是扩大产能的最大障碍之一,部分原因在于培训能力、工作条件有限以及部分生产设施位于偏远地区,这些地区提供的本地劳动力资源有限。
从“电流大战”的辉煌到如今供应链的脆弱,这一历程不仅是技术迭代的缩影,更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的注脚。尽管美国政府已开始通过政策激励与产业协作重振变压器制造,但重建一个涵盖原材料、技术人才、基础设施与高效供应链的完整生态,绝非朝夕之功。如何在开放竞争中平衡安全与自主,在技术迭代中重塑产业韧性,美国的变压器危机将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也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审视全球化角色与本土制造能力的一面镜子。
( 责任编辑: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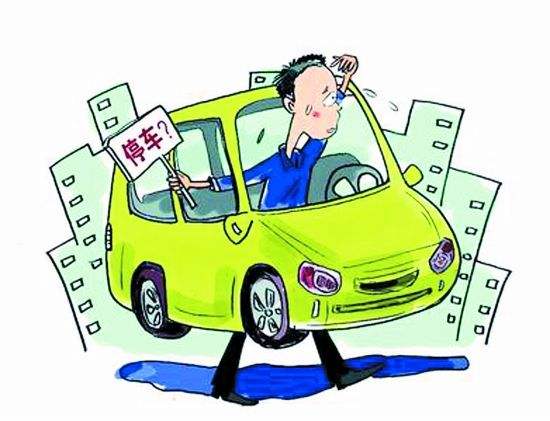 |
|
| 因地施策,破解停车难 |
|
|
| |
|
|

